如果要在二十世紀(甚至直到今日)選出一本厚度最薄卻最有份量的社會科學著作,《叛離、抗議與忠誠》堪稱第一。本書作者赫緒曼曾經提及,有關社會和經濟問題的專書被寫出來,通常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作者在尚未撰寫以前,已經找到答案或精彩論題,至少確定是啟發性的見解;另一種是,作者對問題沒有答案,但想要找到答案的憂戚之心,只有透過書寫才能提供。前一種寫作契機幫助作者把心思聚焦在答案,會以為自己的答案不只可以解決一個問題,而是很多問題;後一種寫作動機從問題出發,引導惶惶困惑之心尋找的不只一個答案,而是多種答案。
【書評書介】《叛離、抗議與忠誠》導論:赫緒曼夢想所繫(上)|廖美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6855
【書評書介】《叛離、抗議與忠誠》導論:赫緒曼夢想所繫(上)
發佈於 3 月 28, 2018
如果要在二十世紀(甚至直到今日)選出一本厚度最薄卻最有份量的社會科學著作,《叛離、抗議與忠誠》堪稱第一。本書作者赫緒曼曾經提及,有關社會和經濟問題的專書被寫出來,通常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作者在尚未撰寫以前,已經找到答案或精彩論題,至少確定是啟發性的見解;另一種是,作者對問題沒有答案,但想要找到答案的憂戚之心,只有透過書寫才能提供。前一種寫作契機幫助作者把心思聚焦在答案,會以為自己的答案不只可以解決一個問題,而是很多問題;後一種寫作動機從問題出發,引導惶惶困惑之心尋找的不只一個答案,而是多種答案。[1]
赫緒曼的著作,多在第二種分類下寫出來。這樣的寫作動力,讓他對問題的求索具有深沉關懷,卻不至陷入悲觀。畢竟,解決問題的答案不只一個,而是有很多可能性。讀者常從赫緒曼看事情的角度發現,被他命名的一些概念,如本書的「叛離」(轉向支持另一機構、產品或信仰)與「抗議」(對現狀提出意見、批評和反對),非常靈動。赫緒曼透過概念的雙向流動,把人與組織的複雜關係聯繫起來,也在其他層面展開,形成一系列不斷擴大的組合反應。
本書的卓越在於,用簡單易懂的詞彙,表達基本和可見的反應,不管透過「叛離、退出、拋棄」或「抗議、表達、批評」,都在捕捉人們糾結於離開或留下之間的反覆——應該退出遠走?還是就地發聲?什麼時候需要在兩者之間切換抉擇?
由於現實世界的選擇並不明確,赫緒曼也透過心理學和社會心理的解析,進一步釐清人與社會的糾葛面貌,做為了解人們選擇的輔助;而「叛離」與「抗議」則分別指向經濟學和政治學的分野,這兩種面對事情的回應,既可混合替換,之間也不互斥。 簡言之,人們很少是頑固的叛離者或純粹的抗議者,有時相互替代,有時採取互補,有時彼此破壞,其中牽涉的是混合與轉換的煉金術。
在赫緒曼的筆下,這本關於幾個簡潔行動概念的書,立刻變得複雜起來。在此提幾個書中闡述為例。比如,從消費者對紅酒、乳酪或小孩教育品質要求的不同,赫緒曼說明,當這些「產品」的品質下降,將帶給不同顧客群不同經濟損失的主觀評估。 就行家紅酒顧客而言,他們的消費者剩餘比較多,願意花費高價購買某一個品牌紅酒,一旦紅酒品質下降,會立刻選擇叛離,因為有其他品牌可以替代。也就是,消費者剩餘比較多的人,選擇叛離的機會比較大。再者,「抗議的力道」則可被需求品質的彈性所決定,當產品品質下降,消費者首先想到的是,要不要叛離換個產品?而不是去影響企業產品的品質。只有消費者決定不換品牌,才比較可能出面抗議品質的低落。赫緒曼問:「在價格上漲即刻叛離的人跟品質下降選擇叛離的人,有沒有可能不是同一批人?」這個提問,馬上讓分析變得繁複有趣,在《叛離》第四章有非常精彩的論述。
再從個人捍衛生活品質的差異,赫緒曼的分析概念,也可用來探究社會流動的問題:「機會平等與向上社會流動的結合,真能確保社會正義嗎?」如果上層與下層階級分歧擴大並且變得僵化,上層如何持續往上流動,下層如何緩緩停滯不動,一般並不容易察覺。另外,以為競爭可以一定程度限制獨占也太理想化,有些情況是透過競爭反而幫獨占排除比較棘手的顧客,讓獨占更舒適,從而更強化獨占。赫緒曼用「獨占型暴政」(monopoly-tyranny)來形容這種不太被注意的獨占形態,它的特質是:「無能者欺壓弱小,懶惰鬼剝削窮人,這樣的事更持久而且更令人窒息,因為它既沒有野心,也可以逃之夭夭。」這種不需負責、不被究責的「獨占型暴政」常發生在國營或國家資助的產業,因為盈虧多由大眾買單,即使競爭也無法改善獨占的局面。
赫緒曼把供給、需求、消費者剩餘、公共財、耐久財、產品品質彈性、獨占、寡占、雙占等屬於經濟學的理論概念,巧妙運用於解析政治行動。不過,這本書相對花比較多篇幅在經濟觀點,以有限篇幅處理政治學家所關注的研究對象——國家。赫緒曼在稍後出版的論文,曾特別把「國家」帶進來,探討人們出走(叛離/移民),對移出和移入國的影響。[2] 可以看到的是,歐洲國家大規模的移民(例如移向北美新大陸),一方面減少歐洲國家內部的社會抗議,另一方面移民在移入的新社會沒有網絡,在當地也比較低調 ;結果呈現,大量移民對移出和移入國的短期影響是減少抗議。另外,可能從人民的出走進一步理解當代民主化的情況嗎?例如,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工人在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初期大規模向法國和德國移入,有促使這些國家更願意通過談判,形成較為民主的程序來留住人民外移嗎?赫緒曼認為這種關係的連結不容易確證,因此獲得的關注不多。不過,異議者離開本國,短期內對威權政權的鞏固顯而易見,這是威權政體處心積慮把異議者驅逐或禁止政敵回國的主因。檢視愛爾蘭人於五〇年代大量出走英國的案例,因為沒有語言隔閡,移出比例非常大,被認為對愛爾蘭國家的存在造成威脅。後來愛爾蘭在一九五八年通過國家經濟計畫,試圖藉由改善經濟政策與條件,防止人民移出與人才流失。赫緒曼提到小國在這方面應變的彈性,跟大國相比,有一定優勢。[3]
《叛離》出版於一九七〇年,但在一九六八年就以單篇論文發表於史丹佛大學行為科學中心。不妨留意,一九六八年正是六〇年代反叛抗議的高峰。不過,叛離、抗議與忠誠的概念本有古典餘韻,赫緒曼進入老派議題,把它們放在消費社會和公民抗議的現況裡,精妙地鍛鑄這些概念。
這書一出版,馬上造成轟動,廣泛被各領域的人閱讀、討論與運用。然而,赫緒曼並沒有提出一套艱澀理論來刻劃現實,而是派遣日常語彙來捕捉行為動力,藉以展現人們的活動其實是在一個流動的、混合的、不完美的現實中運作。世界雖然充斥著「叛離者」,但並不受「純粹競爭」所支配,人們也不能以毫無拘束的「抗議」來維護自己。在選項上,赫緒曼既不鍾情叛離市場,也不偏好政治抗議;一切都是計算, 可能有「最佳」組合,但組合的情況並不穩定。
這裡,我們值得花一點篇幅來談一下《叛離、抗議與忠誠》被寫出來的前情往事。
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家阿德爾曼(Jeremy Adelman)撰寫的赫緒曼傳記於二〇一三年出版,書名取為《入世的哲學家》(Worldly Philosopher),不過,這裡的「worldly」一語雙關,表示赫緒曼在社會科學界的「世界性」與「入世」。一般對赫緒曼的介紹,常從他是哥大和哈佛等名校教授,及在一九七四年進入高等研究院,直到學術生命最後,一直在高等研究院的崇高地位。事實上,他在進入學院之前堪稱坎坷的經歷,更值得了解。
赫緒曼自一九三八年在義大利完成經濟學博士學位,一九四一年元月從歐洲逃離納粹踏上美國領土,到一九五八年寫出《經濟發展策略》,其間二十年,都不算有固定工作,寫完《策略》後,甚至還曾短暫失業,這時他已經四十三歲,還在經濟學門。
難道是初始長期不在學院的二十年,讓赫緒曼相對不局限於學院思考嗎?
[1] 見Jeremy Adelman, 2013. Worldly Philosopher: The Odyssey of Albert O. Hirschm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頁 371。
[2] 見赫緒曼,1981. “Exit, Voice, and the State,” 收入Essays in Trespassing 一書,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頁 246-265。
[3] 赫緒曼引用美國社會學家瑞妮.福克斯(Renée Fox)在比利時社會多年研究的心得,作為想像的啟發。福克斯最初選擇比利時作研究場域,就因比利時是「一個小國……比一個大國更容易從社會學的角度理解。」進行研究多年後,她發現與自己原初的想法完全不符:「如果我現在被要求提出涉及國家規模與社會制度複雜性關係的社會學假說,我會嘗試建議兩者之間存在反向關係;就是國家越小,社會制度反而越複雜!」前揭書,頁265。
關鍵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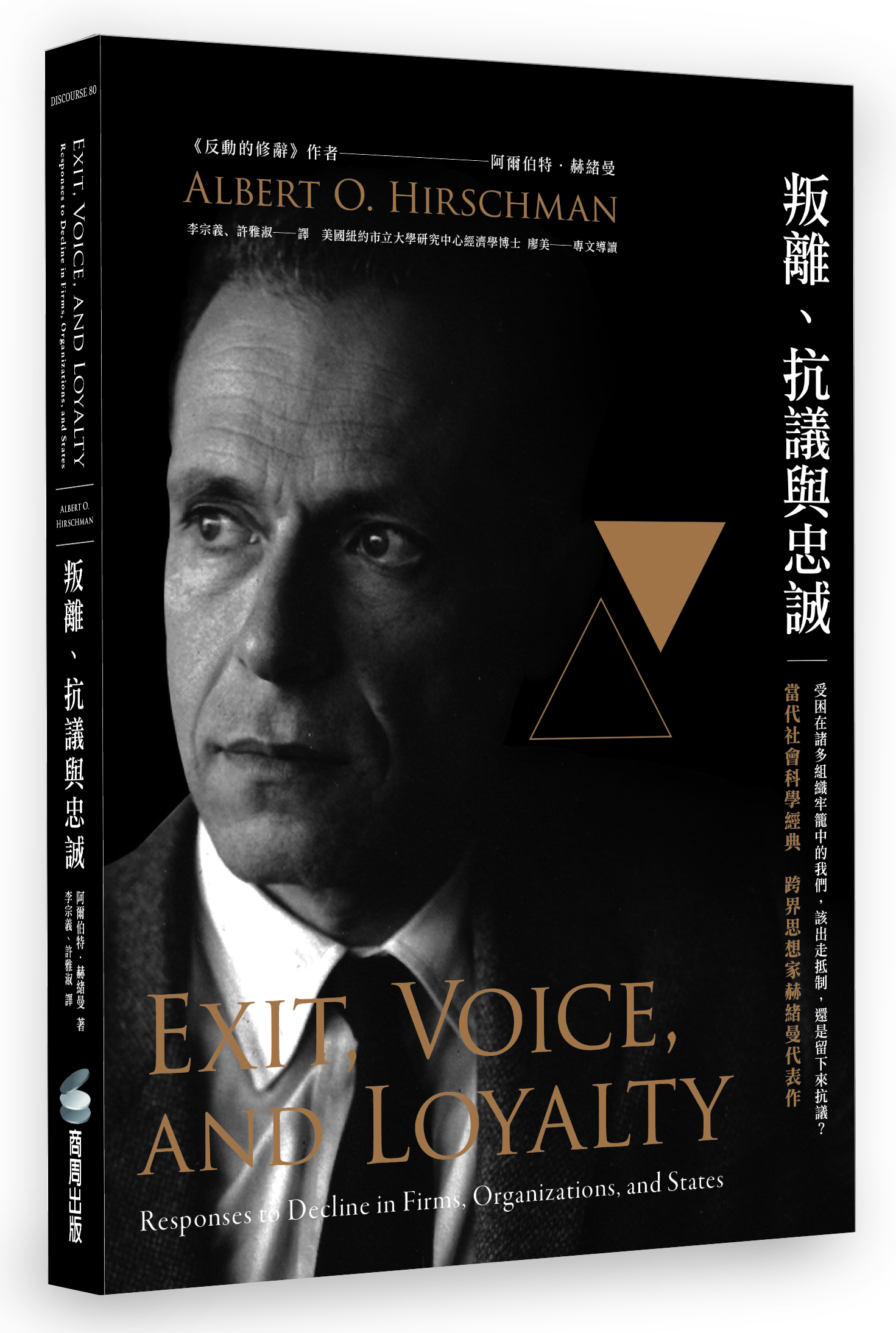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