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真的是一場「正義之戰」嗎?這是一個需要重新回答的問題。
對很多普通民眾而言,北伐的勝利以及此後威權政府的建立,並非福音而是更大的災難。北伐戰爭期間,南方黨軍所宣揚的「國家統一」理想,不過是蔣介石等新軍閥追求權力的遮羞布而已。
【書摘】1927:民國之死|想想論壇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6114
【書摘】1927:民國之死
人氣指數: 1662
發佈於 3 月 12, 2017
自序:天下已逝,邦國難成
一九二七年,對於那個時代的大部分中國人來說,仍然延續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傳統生活方式;而對某些中國人來說,則是他們生命中的重大轉折點。
結婚無疑是人生中最大的喜事,這一年前後結婚的名人有:蔣介石與宋美齡、梁思成與林徽因、羅家倫與張維楨。
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婚禮被譽為「世紀婚禮」,美國《紐約時報》評論說,中國的明星軍人由此與全國最著名的家族之一聯姻,宋美齡也藉此獲得權力。美國《時代》週刊如此評價這樁婚姻:「僅僅一個家族的觸鬚就分別伸向了中國偉大的首任大總統(孫文)、今世的征服者(蔣介石)、位高權重的財政部長(宋子文)以及中國先哲的第七十五代孫(孔祥熙)。」而新成立的南京政府的性質及外交政策,也深受這場婚姻的影響。
如果說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婚姻意味著政治,那麽梁思成與林徽因、羅家倫與張維楨的婚姻就意味著愛情——這兩對新人都是留學歐美歸來,都將在未來中國的文化、教育和學術領域發揮重要作用。在這兩場婚禮的背後,還有一場在前一年完成的婚禮,卻與這兩場婚禮有著草蛇灰線之聯繫,那就是徐志摩和陸小曼的婚禮。
「新月」才子徐志摩因為追求林徽因,決然拋棄妻子張幼儀。等徐志摩追隨林徽因回到中國,才發現林徽因選擇的未婚夫是跟她同樣從事建築學的梁思成。徐志摩燃燒的激情不能熄滅,必須尋找新的對象,他找到了同樣堪稱絕代佳人的陸小曼。徐志摩的父母勉強同意這場婚事,但提出必須由徐志摩的恩師梁啓超作證婚人。梁啓超在婚禮上對這對新人厲聲斥責,心中大概暗自慶幸:幸虧兒子梁思成在愛情長跑中勝出,否則若林徽因嫁給徐志摩,一定不會幸福。所謂「人間四月天」,只有一個月轉瞬即逝的美好光景。
而更為有趣的是,張幼儀離婚之後,留學德國,在獨身時代遇到的第一個追求者居然是也在德國留學的羅家倫。那時,羅家倫與初戀女友張維楨因一場誤會而分開了,張幼儀的堅韌與溫柔深深打動了他。然而,張幼儀拒絕了羅家倫的求愛,這才有後來羅家倫與張維楨的重歸於好。這個世界真是太小了。
幾家歡樂幾家愁,生命在這一年終結(非自然死亡)的人們,更是個個有話要說。
國學大師王國維聽到黨軍北伐節節勝利的消息,毅然赴頤和園昆明湖投湖自盡。此前,王國維可以忍受北洋政府的統治;此刻,卻不願忍受即將到來的國民黨的統治。他留下「以共和始,以共產終」的預言,未來中國政局的走向被他一語成讖。發人深省的是,北伐軍即將打到北京的消息,在清華園引起兩極反應:青年學生欣喜若狂,國學院的「四大導師」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和趙元任卻個個憂心忡忡。
上海工運領袖汪壽華原本是一名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啓蒙的熱血青年,後來成為教育程度最高的上海工運領袖。在蔣介石發起的「四一二」清黨屠殺中,他是枉送卿卿性命的第一人。不可思議的是,汪壽華與殺害他的兇手杜月笙同是青幫大佬。左與右、正與邪,如同川劇「變臉」一般,其身份的錯亂折射出時代的荒謬。
北大教授、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躲藏在蘇俄使館遙控北方的左翼運動。張作霖的軍隊闖入蘇俄使館,將其逮捕并處死。李大釗希望未來的中國是「赤旗的時代」,為此他願意接受蘇俄讓其顛覆本國合法政府的命令,其「賣國罪」的真實性,比之中日戰爭期間汪精衛政權的巨頭們猶有過之而無不及。
藏書家葉德輝螳臂擋車般地對抗湖南農民運動(毛澤東所謂的「痞子運動」),被當作「土豪劣紳」捕殺。康有為死於神秘的食物中毒,其《大同書》生前秘而不宣,他不會想到毛澤東的「紅寶書」將給中國帶來更大禍害。佔領南京的國民黨軍隊,悍然殺害為近代中國教育、慈善事業作出巨大貢獻的美國宣教士、學者、金陵大學副校長文懷恩,「南京事件」儼然是「縮小版」的義和團運動。他們的生命在這一年戛然而止,他們的死亡,或重如泰山,或輕如鴻毛。
十六歲的中華民國夭折了
一九二七年是誕生了十六年的中華民國歷史上一個重大轉折點,甚至是其滅亡之時。
若以一九二七年為分界線,這一年之前與之後,可分為截然不同的「兩個民國」。一九二七年之後的南京政府,拋棄北京中華民國政府之法統,國旗、國歌均被變更。蔣介石雖然血腥清共,南京政權仍亦步亦趨仿效蘇俄體制,以黨國一體化、黨軍一體化、黨政一體化爲依歸。在其冠冕堂皇的五院制當中,具有獨立立法權的國會和具有獨立司法權的最高法院,是不存在的;民選各級官員、代議士的制度和程序,也是不存在的。南京政權實質上是一黨獨裁,卻以「軍政、訓政、憲政」之「三部曲」欺世盜名。胡適只用一句話就戳破了這個泥足巨人:「中國今日之當行憲政,猶幼童之當入塾讀書也,我們不信無憲法可以訓政;無憲法的訓政只是專制。」
北伐戰爭之前,得到世界各國普遍承認的、合法的中華民國政府,並非國民黨的廣州政府,乃是北京政府。北京政府被黨軍以武力顛覆,從此一直遭到勝利一方(國民黨以及後來取代國民黨的共產黨)的肆意妖魔化。實際上,北京政府是辛亥革命所締造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儘管那個時代政局動盪、復辟紛擾、軍閥混戰,且列強凌虐,但北京政府畢竟有三權分立之結構、多黨競爭之格局、各級選舉之實踐,與地方自治之嘗試,以及公民自由之保障(五四運動才可能成功)。那十六年間,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領域均獲得長足發展,理應得到歷史之公正評價。
北洋時代的「舊軍閥」如徐世昌、段祺瑞、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們,比起國民黨時代的「新軍閥」,離文明世界更近。那些爲北洋政府服務或支持北洋政府的文化精英和技術專家(少數後來繼續爲南京政府服務),皆為一時之選,如同群星璀璨:顏惠慶、顧維鈞、湯化龍、章太炎、梁啓超、蔣百里、丁文江、王之江、陳遺陶等人,哪一個是南京政府可以培育出來的?而完全是匪幫的中共集團,就更等而下之了。
胡適指出:「北伐的主要社會基礎,就是邊緣知識分子。」一九二七年之後取代北洋軍人支配中國政治的,是由邊緣知識分子形成的「黨人」。如果說蔣介石是城市和沿海的邊緣知識分子(流氓),那麽毛澤東就是農村和內陸的邊緣知識分子(流氓),在他們之間「比好」毫無意義——這恰恰是中國和海外多如牛毛的「民國粉」、「國(國民黨)粉」和「蔣(蔣介石)粉」們的精神支柱。北伐大大加劇了清末民初思想與社會的「權勢轉移」(羅志田語),造就了蔣介石和毛澤東這樣舊學和新學都不通的人從邊緣佔據中心位置。所以,北伐剛剛完成「統一大業」,胡適就哀嘆中國的民族自救運動已經失敗,中國仍然沒有一個重建民族認同的文化基礎,因而不可能建立起社會和政治的重心,「再造文明」的理想也就成為遙不可及的水月鏡花。
跟此前的北京政府相比,南京政府是一個全新的政權。早在一九四九年共產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顛覆國民黨的「國民政府」之前,一九二七年國民黨的黨軍北伐就已顛覆了在淒風冷雨中苦苦掙扎十六年的中華民國。所以,蔣介石而非毛澤東,才是中華民國真正的「顛覆者」。蔣政權並沒有繼承中華民國之法統,它敗退台灣之後,更沒有資格高舉中華民國的神主牌,並自詡為「自由中國」。
北伐與清黨:二十世紀中國災難的源泉
一九二七年,最重大的歷史事件是北伐和清黨。
國民黨的歷史敘事將北伐視為不朽之盛事、千古之偉業;共產黨則至少肯定前半段的北伐——蔣介石清黨之前的北伐,因為共產黨在其中也出了不少力。
一九二七年春,生於蘇州的美國傳教士費吳生(George A. Fitch)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北伐戰爭不僅是像美國南北戰爭一樣的內戰,而且是集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及文藝復興於一身的『大運動』。」那個時代到中國的西方宣教士,大都屬於傾向「社會福音」的左派,費氏亦不例外。當瘋狂排外的南京事件發生之後,他的這種樂觀的評價會不會改變呢?
北伐真的是一場「正義之戰」嗎?這是一個需要重新回答的問題。
對很多普通民眾而言,北伐的勝利以及此後威權政府的建立,並非福音而是更大的災難。北伐戰爭期間,南方黨軍所宣揚的「國家統一」理想,不過是蔣介石等新軍閥追求權力的遮羞布而已。在歷史轉折關頭,並不是所有人都傾心支持北伐,不同的態度和聲音——包括被主流史觀認為是「反動」的人物,如章太炎、王國維、梁啓超、胡適、周作人、徐志摩、陳寅恪、丁文江、葉德輝等知識界名流對黨軍北伐的恐懼和反對——都有其合理性存在,都有被記錄、思考、探究的價值。
支撐北伐戰爭的意識形態,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逐漸形成的極端民族主義、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等偏執而邪惡的學說。北伐戰爭的殘酷性超過了此前軍閥間的內戰。軍閥的內戰還停留在古典狀態,通常不會殺戮俘虜,更不會槍殺對方的高級將領。失敗的軍閥一般通電下野,然後去租界當寓公。北洋時代少有槍殺高級將領的事件,始作俑者往往自己要付出生命代價。比如,徐樹錚槍殺陸建章,後來爲陸建章的姪女婿馮玉祥所殺;孫傳芳槍殺施從濱,後來爲施從濱的女兒施劍翹所刺殺。然而,北伐中的黨軍不講任何規矩和原則,偏偏以殺俘虜和殺高級將領來製造恐怖氣氛。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由國民革命軍、國民黨黨部和部分民眾組成「江西人民審判委員會」,將在去年十一月南昌戰役中被俘虜的孫傳芳部下高級將領張鳳歧、唐福山、岳思寅、白家駿、侯全本、蔣鎮臣、楊賡和、李彥清、王良田等人,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這是民國以來戰爭中槍殺高級將領最多的一次。
清黨則是一個更具爭議性的事件。今天,有不少反對共產黨的所謂「民主人士」,對國民黨當年殺共產黨殺得不夠、沒有斬草除根而感到遺憾。似乎如果國民黨在一九二七年殺掉更多共產黨,就能確保一九四九年不至於被共產黨趕到台灣。然而,邪惡的方法從來不可能達致美好的目標。當時,《大公報》即就清黨事件發表評論說:「政治刑事犯而付軍法,且特立機關,執行殺戮,此種制度爲任何文明國家所不許,亦古來專制政體下所從無有之。惟民國後之中國耳。」清黨運動也留下致命的後遺症:它導致知識分子的分化和分裂,尤其是蔡元培和吳稚暉等人在清黨中的表現,加劇了知識精英退出社會領導位置的過程;邊緣知識分子逐步走上政治運動的領導地位,與知識精英分子的某些自損形象的行為不無關聯。胡適敏銳地發現,國民黨「以思想殺人」而「失去一般青年的同情」,恐怕正是其由興盛走向衰落的重要轉折點。
北伐和清黨並不能解決近代以來中國面臨的根本問題,即歷史學家唐德剛所說的如同「出三峽」般的國家建構和民主轉型。蔣政權在名義上實現了全國統一,實際上卻帶來更酷烈的戰禍和黨爭,中原大戰及剿共戰爭,次次殺人如草不聞聲。
此後二十二年,國民黨政權腐敗無能,坐視農村經濟凋敝,又與城市新興資產階級爲敵。於是,民間的左派激進思潮節節升高。國民黨不願接受自由主義價值,除了回歸傳統儒家專制主義以及向德國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取經之外,提不出任何吸引人心的意識形態,最終失去民心。
靠清黨的方式無法消滅共產黨。一九二七年,共產黨在城市發起的暴動暫時受挫,但以共產主義思想包裝的、毛澤東式的土匪割據模式終將烈火燎原。
分裂的中國,人民有更多的自由和快樂
北伐之後,南京政府建立並完成了中國形式上的統一,這個過程符合「大一統是歷史之必然趨勢」的大中華史觀。然而,「必然統一」是歷史的真相嗎?惟有「統一」才是中國人的最高信仰嗎?
南京政府及蔣介石權力所能行使的區域,在一九二零年代末期僅有長江下游及華南少數的幾個省市。清帝國崩潰之後,帝國傳統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作為近代民族國家的中國遲遲不能成形,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在「天下」與「國家」的兩極之間搖擺。
一九二七年,清帝國的「藩屬國」或「羈絆國」如西藏、北蒙古等已取得實質性的獨立地位,處於半獨立狀態的有滿洲、新疆、青海、寧夏等地,處於高度自治狀態的則有山西、陝西、四川、兩廣、雲貴等地。在獨立、半獨立或高度自治的狀態下,某些區域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以及民眾之生活品質優於昔日中央的直接控制。這段不同區域「各自為政」真實的歷史,足以解構「統一是民眾福祉之保障」的虛假史觀。
我不認同梁啓超在清末生造出來的「中華民族」之概念,而以「住民自決」和「民族自決」的現代普世人權觀念來審視所謂「少數民族」的國家和族群認同。我講述了那些爲各自民族的獨立而奮鬥的人物的故事,並盡量還原他們本人的想法:作為藏族人的土登嘉措(第十三世達賴喇嘛)、作為維吾爾族人的穆罕默德·伊敏、作為滿族人的川島芳子(前清公主顯㺭),與作為蒙古族人的德穆楚克棟魯普(德王)……他們拒絕接受「中國人」的命名,至多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鄰居」。如果中國人要對他們進行殖民統治,他們自然將中國人看作「敵人」。
最有趣也最具悲劇性的人物無疑是旅居上海的台灣人劉吶鷗,他是超越「一元」國族認同的「世界人」,正如他所引領的新感覺派小說和電影的潮流,他的觀念領先於他的時代,甚至今天的時代。在血緣上,他是華人;在國籍上,他是日本人;在出生地上,他是台灣人;他的母語是閩南語;他的文化品位是日本文學和法國文學;而他喜歡居住的城市是上海。劉吶鷗參與汪精衛政權的文化工作,並不覺得這是「賣國」之舉,而只是做一件自己喜歡的事情而已。他卻被國民黨特務以「漢奸」的罪名暗殺。
這是一群需要為之「正名」的人物,嚴肅的歷史寫作者,當爲他們的言行和選擇提出更接近歷史真相的解釋,以此恢復歷史與精神本身的多元性與豐富性。
個體的自由、尊嚴和幸福,高於國家、民族、階級等宏大敘事。北洋時代,中央政府的衰敗意外地爲民間社會的發育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生機勃勃的民間社會是那個時代最大的亮點。我要講述的是人的故事,尤其是那些過去的歷史書中無法歸類的人物的故事。比如:以陳光甫、盧作孚、張幼儀為代表的商人、銀行家、企業家(即「民族資產階級」),以劉大鵬為代表的農民(在中國的主流歷史敘述中,農民一直是「失語者」),以及作為虔誠的基督徒、醫術高超的醫生和女性解放的先驅的石美玉,他們以堅韌不拔的努力捍衛自身信念,成為那個時代值得被記取的標竿,他們應當被請回歷史的中心位置。
近代以來的中國,已非閉關鎖國、唯我獨尊的「天朝」,從船堅炮利到新式軍隊,從汽車火車到洋火洋燈,從西裝革履到大學中學,從國會憲法到民主自由,外來因素之影響無遠弗屆。我將若干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的故事納入其中:代表蘇俄勢力的鮑羅廷曾經對北伐的勝利、國共兩黨的分合一言九鼎,最終以失敗者的身份回到蘇聯,成為史達林遠東政策失敗的替罪羊並死於古拉格集中營;英國駐香港總督金文泰爵士本身是一名漢學家,卻能以外交家的手腕平復省港大罷工,並爲香港政治改革、教育和醫療等民生事務作出重大貢獻;擔任美國駐天津的十五步兵團營長的史迪威不會料到,在十多年之後的太平洋戰爭中,他將被任命為美軍在中緬戰場的最高指揮官,並與蔣介石針鋒相對。從這些人物在中國的活動可以看出,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進程,已然無法擺脫外力所發揮的或正面或負面作用。
我仿效歷史學家黃仁宇《萬曆十五年》之寫法,描述二十五位核心人物(兼及七十五位次要人物,共有一百人登場亮相)在一九二七年前後生命歷程、政治觀念及精神取向之變遷。雖然是小說般生動靈活的筆調,卻有成為思想史的企圖:在人物的交互作用中,探討近代中國由帝制(天下)向憲政共和(民族國家)的轉型為何全盤失敗,美國式的「聯省自治」為何無法在中國成功複製。
回首歷史,立足現實,眺望未來,希望這本書能啓發更多人為尚未完成的中國民主化以及華人文化圈之精神重建,尋找一條可行的路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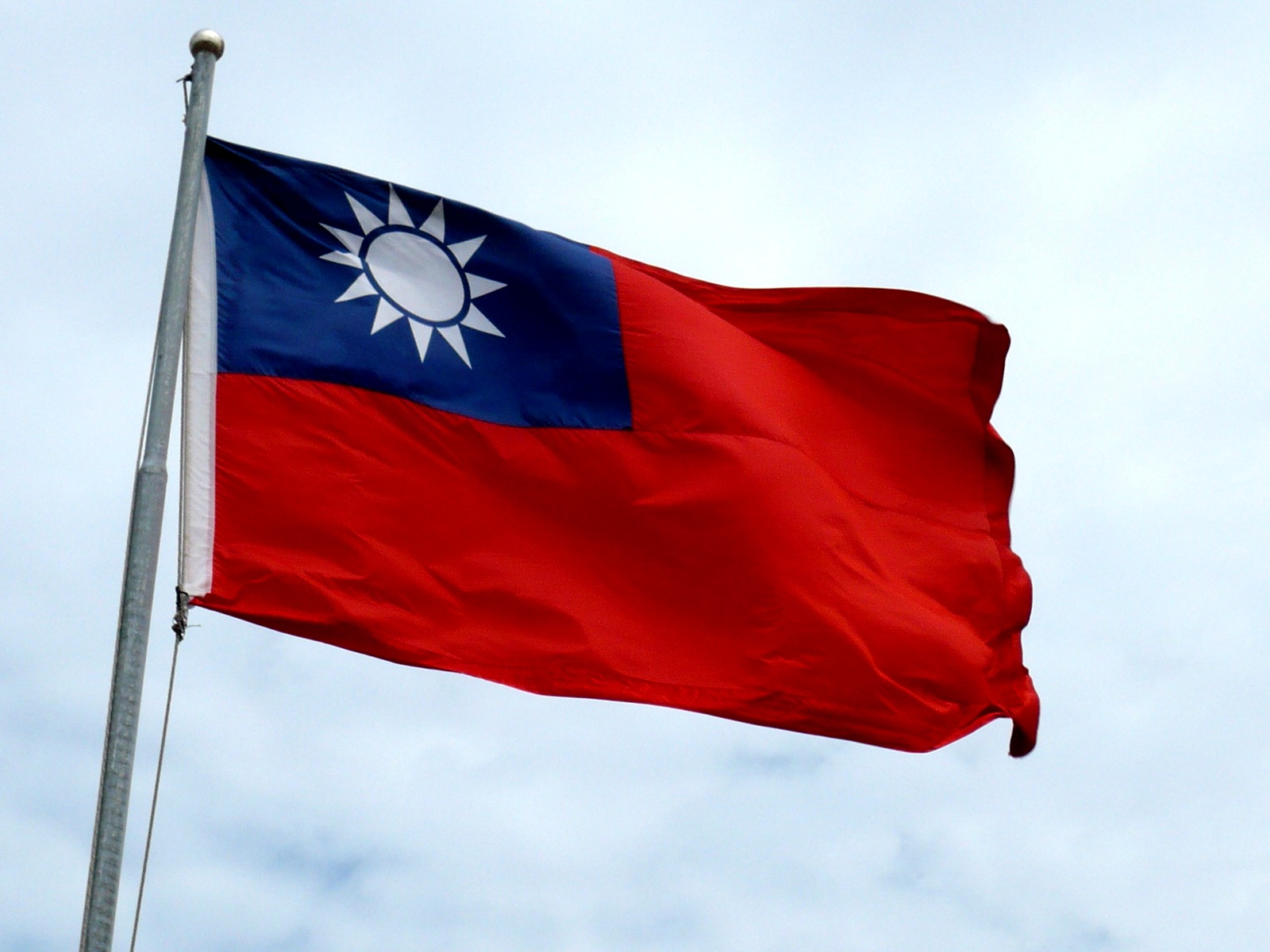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