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e-info.org.tw/node/218840?utm_source=%E7%92%B0%E5%A2%83%E8%B3%87%E8%A8%8A%E9%9B%BB%E5%AD%90%E5%A0%B1&utm_campaign=0b74f99504-EMAIL_CAMPAIGN_2019_07_26_02_54_COPY_01&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f99f939cdc-0b74f99504-84956681
鐮刀除草 揮刀如太極 讓光陰倒流回沒有割草機的年代
文:約翰•路易斯─斯坦伯爾 (John Lewis-Stempel)
好玩的是,一些小事就能讓光陰倒流。幾年前,我把曳引機駕駛艙的門和後車窗拆了,這樣坐在曳引機裡面比較涼爽,也能獲得更真切的體驗。此外,把多餘的裝飾拆掉,也更容易逃生;駕駛艙有一次電線走火,我很快就跳出車外逃命。儀表板現在看起來仍像達利的畫作。每當我坐進這個幾乎露天的駕駛艙,就會想起爺爺的一張照片。照片中,他正開著一輛福格森T20,別過頭去專注看著後面犁的地。T20閃閃發亮,下過雨後更是如此。爺爺裹著一件灰色雨衣,車上沒有駕駛艙。
我從爺爺的年紀和那輛福格森的新穎程度來判斷,猜測這張照片是在1958年左右拍攝的。他們大約在一年後扼殺了農業,在曳引機上加裝駕駛艙。農夫再也無法經歷風吹雨淋,甚至不能親近土地。農夫現在只要坐在一個有暖氣和收音機的小小行動辦公室,操縱控制桿即可。我曾經坐過有空調系統和電漿電視的曳引機,你大可把腳抬高,一切都交給電腦處理。
由於曳引機不能180度轉彎,因此割草和犁地時都是以橢圓形來進行,割到草地的盡頭就大幅度轉向。最終,曳引機的平行車痕會相連在一起。
用棒狀割草機喀哩喀哩割了20分鐘後,我已經完成半英畝,割好的草躺在地上,就像絢麗的都鐸式長辮子,中間交織著毛茛的黃、菽草的紅、百脈根的橘黃,並由剪秋羅的粉紅以及錐足草、繁縷和卷耳的白點綴。割下的黃花茅散發濃烈的香氣,足以掩蓋國際牌引擎蓋排氣管冒出的藍色柴油煙霧的味道。太陽高掛在一片純樸的藍天上,就像創世的第一天。
不久後,田園的美好意境在一陣刺耳與混亂之中戛然終止。割草機撞到石頭了(是的,很有可能是我的鼴鼠丟出來的)。其中一個切割器彎了,另一個斷得支離破碎。
我回到屋子裡,花了一小時上網找替代品。我能找到最好的價格是一個339英鎊的二手貨,可是運送時間是個問題:最少要三天。於是,我打電話問鄰居是否可以商借割草機,但他們的不是不合適,就是他們要使用。他們說的一點也沒錯,從敞開的窗戶,我可以聽見丘陵和谷地充斥著割草機的聲音。
我想,我知道自己要做什麼。甚至,我不敢肯定那顆搞砸大事的石頭不是我透過某種超自然的能力安排的。
在牛棚裡,一把鐮刀和其他很久以前人們所使用的工具擺在一起。一把死神使用的鐮刀,有著山胡桃木製成的蛇狀刀柄和兩個握把。我決定徒手割草。
好玩的是,一些小事就能讓光陰倒流。我把刀柄抵在地面,磨刀石斜斜地朝上拂過刀刃,將刀鋒磨利。我看見父親的身影套疊在我身上,看見他像《三劍客》的人物達太安那樣,用鋼鐵磨利星期天要用的切肉刀。
英國的鐮刀像個怪物,有著厚重的白蠟樹握把和粗鋼刀刃。這把鐮刀樣式古老,是我們搬進來時在牛棚找到的。此樣式是為20世紀初的赫里福德人所做,也就是身高約5尺6寸的人。但是,白蠟樹刀柄的蛀洞很多,於是我把用金屬夾固定在刀柄上的握把移動4英寸以上。好的鐮刀就像好的獵槍,必須去迎合每一個人的手。在那個我永遠尋求不到的完美世界裡,鐮刀應該要客製化。
用鐮刀割草的訣竅就是要讓刀刃平貼地面,離地表只有一毫米,接著以圓弧的方式揮動鐮刀。揮動時要彎膝,重心(若是右撇子的話)從右腳轉移到左腳。用鐮刀割草的人姿勢如果正確,看起來就像是在打太極。我會知道這些,是因為我用過鐮刀。少年時期,我會用鐮刀割除我們家果園樹與樹之間的草,因為這些地方很難使用割草機。自那時起,我就一直使用鐮刀除草。
然而,這天早上割草時,大部分的草都順著鐮刀低頭,然後又彈回來,一邊咯咯笑。隨著每分每秒逝去,草變得越來越乾,更無濟於事;應該要選在早晨露水多的時候用鐮刀割草。
此外,不停揮舞鐮刀需要非常大的力氣。由於刀刃每10分鐘就要磨利一次,我便開始希望預定的磨刀時間趕快來臨,讓我能把磨刀石從水桶中拿出來,沿著刀刃拂過。我的手也開始起水泡了。我腰酸背痛,臉被曬得烏漆抹黑;說得不客氣一點,我看起來就像在貝尼多爾姆度假的英國佬。我還割傷了手指,因為我愚蠢地劃過刀刃,想確認刀是否磨得夠利了。在大太陽底下工作兩個小時後,我只割了四分之一英畝左右。若是用曳引機,只需要五分鐘,甚至不到五分鐘。
佩妮像天使般從汗水瀑布中現身,帶了一杯熱茶。她苦笑地問:「進展如何?」
我大聲說:「棒極了!」我不是在說笑。除了接生小牛之外,過去這十年的農作從未帶給我這麼大的滿足感。
我處在近乎狂喜的狀態中。我割下的草整齊地在鐮刀圓弧的左側形成一列列的乾草列,在近距離的狀況下,黃花茅的氣味之強,讓我覺得這一定是住在世外桃源的人使用的除臭劑。然而,讓我哼起歌來的,是割下的草的模樣與觸感。我現在重拾了用鐮刀割草的技巧,一片片割下的草葉如絲綢般滑落,互相堆疊,就像是用玻璃製成般精巧。
用割草機割下的草很多都被壓碎了。先前,我以為這是好事,因為碎裂的草可以更快釋出溼氣,畢竟乾草一定要乾燥嘛。但,我現在割的草給予我不同的啟發。我可以看得到、聞得到它的品質。
那天下午,我用耙子翻動乾草列。
我搜尋記憶的迷宮,想找出我曾在哪裡讀到一段關於徒手製作乾草的好處,最終在約翰‧史都華‧科里斯的《蟲子原諒犁》[註]找到了這段文字。這本書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寫的自傳,講述他在土地上勞動的記事:
農業勞動者很少會讚美工作,或承認自己享受工作方面的任何事情。除了年紀大的人以外,無人抗拒機械設備的引入。然而,製作乾草卻是例外——至少這裡是如此。人人都討厭現在的製乾草工作,讚美昔日的方式。在當時,製乾草被當作是在度假,全家人都在草場上野餐,更別提那一大堆的啤酒了。
[註]約翰‧史都華‧科里斯(John Stewart Collis, 1900-1984),愛爾蘭傳記作家、田園作家,也是生態保護運動的先驅。《蟲子原諒犁》(The Worm Forgives the Plough)一書根據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務農經驗寫成,是自然書寫的經典之作。

一草一天堂:英格蘭原野的自然觀察MEADOWLAND:
The Private Life of an English Field
作者:約翰•路易斯─斯坦伯爾/繪者:麥凱拉•阿爾蓋諾
譯者:羅亞琪
出版:三民書局 2019年5月 出版
定價:35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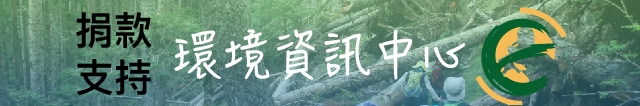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